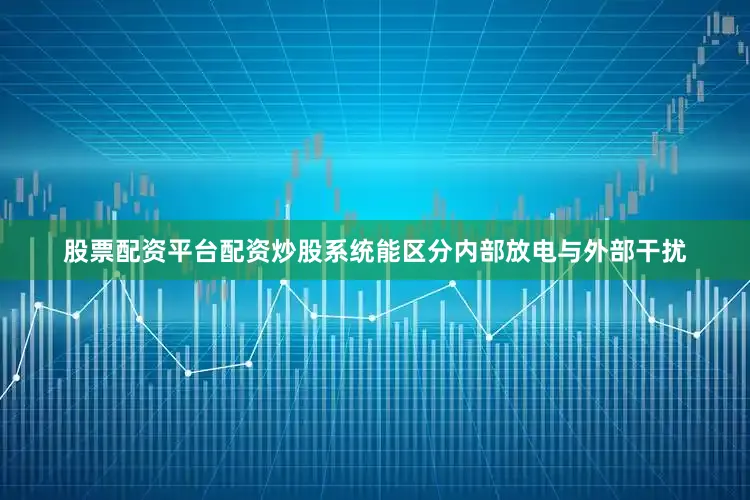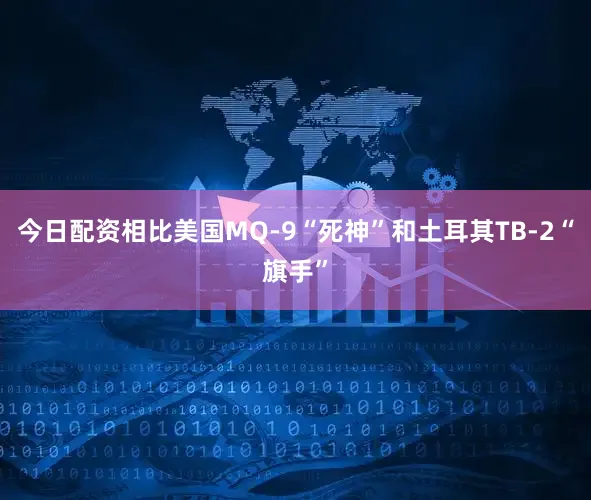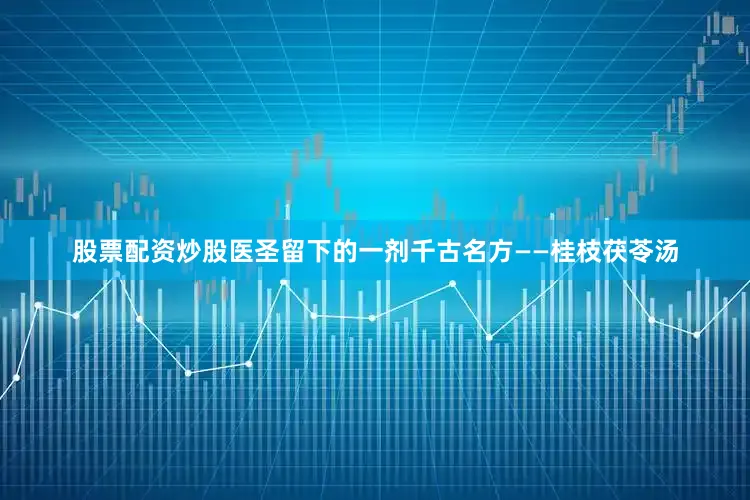01
“小雨?小雨!开门!”
浴室门反锁着,水声哗啦啦地响。我用力拍打着门板,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。已经二十分钟了,这不对劲。
“妈妈在叫你,听见了吗?”
我的声音开始发抖,手指无意识地KOU着门框上的油漆。
没有回应。
我转身冲向储物间,翻箱倒柜找备用钥匙。剪刀、胶带、螺丝刀——为什么东西总是需要的时候就不见了?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,后背渗出一层冷汗。
找到了!钥匙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当我颤抖着打开浴室门时,眼前的景象让我的血液瞬间凝固。十六岁的女儿蜷缩在浴缸角落,手腕上几道鲜红的划痕触目惊心。
“小雨!”
我扑过去抓住她的手腕,用毛巾死死按住伤口。她的皮肤冰凉,眼神空洞地望着我,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。
“为什么...为什么要这样...”
展开剩余91%我的眼泪砸在她苍白的脸上。
救护车的鸣笛声划破夜空。在急诊室外的长椅上,我紧攥着女儿的学生证,照片上的她笑容明媚,与现在判若两人。医生的话像钝器一样砸在我心上:
“中度抑郁,伴有自伤行为,需要立即干预治疗。”
丈夫赶到医院时,天已经亮了。他西装革履,身上还带着机场的寒意。
“怎么会这样?”
他搓着脸,眼睛里布满血丝。
“你一个月在家几天?女儿变成这样你都不知道!”
我压抑的怒火突然爆发,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。
丈夫颓然坐下:
“公司那边项目正在关键期...”
“永远都是关键期!”
我咬紧牙关,把涌到嘴边的更多指责咽了回去。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。
回到家,我把所有尖锐物品锁进抽屉,连厨房的刀具都收了起来。小雨的房门紧闭,我贴在门上听了会儿,只有微弱的音乐声。我轻轻敲门:
“妈妈煮了粥,要不要...”
“别管我!”
一个枕头砸在门上的闷响打断了我。
餐桌上,八岁的小阳怯生生地问:
“姐姐生病了吗?”
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:
“姐姐只是...心情不好。快吃吧,上学要迟到了。”
送走小阳后,我瘫坐在沙发上,SJ屏幕亮起——公司群里的消息不断弹出。我深吸一口气,拨通了主管的dianhua:
“王总,我想请个长假...家里出了点状况。”
接下来的日子,我就像惊弓之鸟。白天,我到处查找怎么让抑郁的孩子走出来,晚上竖起耳朵听隔壁房间的动静。小雨的作息完全颠倒,白天拉紧窗帘睡觉,晚上通宵玩SJ。我每隔一小时就去敲门,端着水果或热牛奶,生怕她再做傻事。
“今天天气不错,要不要出去走走?”
“你老师打dianhua问你怎样了。”
“你最喜欢的奶茶,趁热喝...”
我的关心像雨点般落下,却只换来更厚的墙壁。小雨开始用耳机隔绝外界,看我的眼神充满戒备和烦躁。一次,当我第五次询问她是否想吃晚饭时,她突然抓起水杯砸在地上。
“你能不能别烦我了!你让我连呼吸都觉得累!”
玻璃碎片四处飞溅,我站在原地,感觉自己的心脏也被摔得粉碎。
那天深夜,我被客厅里压抑的啜泣声惊醒。循声走去,发现小阳蜷缩在沙发角落,小脸哭得通红。
“宝贝怎么了?做噩梦了?”
我抱住他单薄的身体。
“妈妈是不是只爱姐姐,不爱我了?”
他抬起泪眼朦胧的脸,
“你都不陪我写作业了...我考试得了满分你也没看...”
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。是啊,上次家长会是谁去的?小阳的生日礼物我准备了吗?这段时间我完全忘记了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母亲。
回到卧室,我盯着天花板直到天亮。我以为自己在拯救一个孩子,却让全家都窒息了。这种24小时的高度警觉不仅耗尽了我的精力,似乎也让小雨更加痛苦。我到底哪里做错了?
02
“小雨妈妈,您看起来非常疲惫。”
辅仁家庭教育的心理咨询师刘老师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现实。
我攥紧纸巾,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:
“刘老师,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...我女儿...”
五十分钟的倾诉后,刘老师暂停了记录:
“我能感受到您作为母亲的爱与焦虑。但您有没有发现,您的‘拯救’模式可能恰恰加重了小雨的症状?”
我愣住了:
“什么意思?难道我不该关心她吗?”
“关心不等于控制。”
刘老师的声音温和而坚定,
“您提到小雨两岁就被送到爷爷奶奶家,直到小学才回来。这种早期的分离可能造成了她对亲密关系的矛盾心理——既渴望爱,又害怕被抛弃。”
我的指甲无意识地掐进掌心。那段记忆一直是我心中的隐痛。当时刚生完小阳,我产后抑郁严重,丈夫又经常出差,实在无力照顾两个孩子。
“现在您全天候的监控,可能唤起了她童年的被抛弃恐惧。”
刘老师继续道,
“她会想:‘妈妈现在这么紧张我,是不是因为我又要失去她了?’这种焦虑反而加重了她的抑郁。”
我如遭雷击。原来我的过度补偿,竟成了压垮女儿的又一重负担?
“那我该怎么办?总不能不管她吧?”
我的声音颤抖着。
刘老师停顿了一下,说:
“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'有意识的低度参与'。不是冷漠,而是在保持日常陪伴的同时,给孩子足够的心理空间。”
她建议我先修复自己的情绪:
“您现在的状态就像一个不断漏水的容器,怎么可能接住女儿的情绪?父母要先学会自我关怀,才能成为孩子稳定的依靠。”
临结束时,刘老师推荐了几本书和情绪管理练习。准备做晚饭时,我发现小雨竟然在厨房倒水喝。我们四目相对,她迅速移开视线,拖着步子回了房间。
我深吸一口气,没有像往常一样追上去问东问西。而是拿起SJ,给久未联系的好友发了条消息:
“明天有空一起跑步吗?”
03
改变比想象中艰难。
第一次晨跑,我每跑几步就要看SJ,生怕错过小雨的消息。好友拍拍我的肩:
“放松点,你女儿十七岁了,不是七岁。”
“可我习惯了事事以她为中心...”
我喘着气说。
“那你自己呢?”
好友反问,
“我记得你以前可爱写生了,还说要办画展呢。”
我沉默了。是啊,那个热爱绘画的我去哪儿了?自从有了孩子,我的身份就只剩下“妈妈"这一个标签。
回到家,我翻出尘封多年的素描本,坐在阳台上画起窗外的梧桐树。笔触生疏却让我感到久违的平静。小雨不知何时站在了身后。
“妈,你还会画画?”
她的声音里有一丝惊讶。
我心跳加速,强装镇定:
“嗯,年轻时学的。要试试吗?”
她犹豫了一下,摇摇头走开了。但这次,我没有感到挫败。至少,她主动和我说话了。
改变在细微处发生。我不再每小时查房,而是固定晚饭时间全家人一起吃饭;不再追着小雨问感受,而是在她情绪稳定时简单分享我的日常。奇怪的是,我越是放松,她越愿意走出房间。
一个雨夜,我正在整理求职简历,SJ突然响起。屏幕上显示“小雨来电”,我的手一抖,差点摔了SJ。
“妈...”
dianhua那头的声音带着哭腔,
“我觉得自己要疯了...”
我握紧SJ,想起刘老师教的"情绪容器"理论:
“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,愿意和妈妈说说吗?”
“家里太闷了...我...”
她突然警觉起来,
“你是不是又想劝我回学校?”
我深吸一口气:
“这是你自己的决定。妈妈当然会担心,但更希望你开心。”
停顿片刻,我又轻声问,
“能告诉妈妈,是什么让你这么痛苦吗?”
dianhua那头沉默了很久,然后是一阵压抑的抽泣。那天晚上,小雨断断续续说了很多:对学业的恐惧、被同学孤立的委屈、甚至还有对小阳的嫉妒...
“你们把他带在身边长大,却把我扔给爷爷奶奶...”
我的眼泪无声滑落。原来这些年,她心里积压了这么多伤痛。我没有辩解,只是轻声说:
“对不起,妈妈那时候太无力了...但妈妈真的很爱你。”
那次谈话后,小雨的情绪明显平稳了许多。她开始按时吃饭,偶尔还会帮小阳辅导作业。有一天我下班回家,发现她竟然拉开了客厅的窗帘,阳光洒满整个房间。
“面试怎么样?”
她头也不回地问,手里摆弄着我买的向日葵。
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,半晌才找回声音:
“挺顺利的...下周一入职。”
“哦。”
她顿了顿,
“那挺好的。”
简单的对话,却让我红了眼眶。原来真正的康复不是我把她拉出黑暗,而是她自己愿意走向光明。
上周,小雨主动提出想回学校看看。站在校门口,她紧张地攥着书包带子。我克制住拥抱她的冲动,只是轻轻捏了捏她的肩膀:
“晚上想吃什么?妈给你做。”
她转头看我,阳光照在她年轻的脸上,眼睛里有了久违的光彩:
“都行...你做的我都喜欢。”
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:爱不是捆绑,而是守望;不是拯救,而是相信。当我终于学会放手,女儿反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力量。
发布于:安徽省启灯网配资,配先查配资,福建股票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